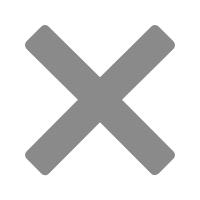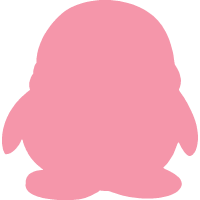-
加班后,我得知了爸爸的第二个家
本书由果悦文化_好看的言情小说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1
大年三十,我被临时叫去顶替同事在抽血窗口值班。
突然排队的队伍里插进一个小女孩,陪同的中年男人带着口罩低声催促。
“麻烦插下队,孩子赶时间。”
见后面人没有反对,我按流程核对信息。
“是许愿小朋友的骨髓配型专用血样吗?”
女孩乖乖伸出胳膊,男人却突然伸手挡住针头。
“等等,我们今天不做了。”
我心里骂着神经病,抬头时发现人已走远,检查单落在台前。
监护人签字“李国明”正对着我。
那是我爸爸的名字,笔迹我认得。
我掏出手机,手指冻得发僵。
“爸,你今天在单位值班吗?”
电话那头传来医院特有的广播声,他停顿了三秒。
“……是在单位啊。”
我沉默不语,挂断电话后,我调出医院系统后台,输入了许愿的名字。
“患者许愿,配型需求方:李国明。关系父女。”
1
“李护士?还做吗?”
后面排队的大爷不耐烦的探过头问。
我猛地回过神,才发现自己撑着台面的手指关节已经捏得发白。
“抱歉,稍等。”
我强迫自己继续完成剩下的工作,脑子里全是爸爸刚才的话。
交班时间一到,我冲进更衣室,锁上门,才敢把那张纸重新拿出来。
“患者:许愿,年龄:6岁,诊断: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”
“配型需求方:李国明。关系:父女。”
“父女”。
这两个字烫得我眼睛生疼。
我掏出手机打开医院内部系统输入了“许愿”的名字。
更详细的病历页面跳出来。
就诊记录最早是九个月前。最近一次是三天前,门诊,开了新一轮的化疗药物。联系人电话一栏,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。
地址是:翠湖苑1号楼8单元602。
这不是我们家的地址,也不是爸爸单位宿舍的地址。
我盯着那个地址,脑子使劲回想。
九个月前正是爸爸开始频繁“加班”、“出差”的时候。母亲还心疼他,说公司今年项目多,让我少去烦他。
我打开地图软件,输入那个地址。
距离医院8.5公里,一个叫“翠湖苑”的中档小区。
我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大楼,拦了辆出租车。
“师傅,去梧桐路,翠湖苑。”
路上我死死攥着口袋里的检查单,双手合十的祈祷自己想的千万不要成真。
我来到小区带上口罩眼睛躲在侧面一棵粗大的香樟树后。
就在我快要被冻僵,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地方,或者这一切只是一场荒谬的误会时。
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,出现在了小区里。
是爸爸。
他上了楼出现在了楼上窗户里。
他弯下腰,轮廓清晰。
他在摸那个小女孩的头。
很轻,很温柔。
小时候我发烧,他也会这样摸我的额头,但近些年,这样的触碰越来越少,他总是很忙,摸头变成了敷衍的、快速的一拍,注意力似乎总在别处。
原来,他的温柔和时间,并没有消失。
只是给了别人。
我忍住眼泪举起手机,镜头有些抖,但我还是拍下了那扇窗户,拍下了那三个依偎在一起的身影。
我不知道在树下站了多久,直到晚上窗户的灯光熄灭父亲也没有出来。
看来爸爸今晚不会回家了。
想到妈妈还在家里等着过年。
我拖着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双腿挪出了小区。
回家的路上,我努力平复好心情,试图让脸上的表情自然一点。
“晚晚回来啦?”。
母亲系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,脸上带着笑意。
“正好,我刚把饺子煮上。你爸刚发消息说单位临时有事,今年又得晚点,让咱们先吃。”
我张了张嘴想告诉她实情。
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。
我用力闭了闭眼,把即将冲口而出的真相咽了回去。
“我去洗个手。”
转身走向洗手间时,眼泪终于忍不住。
我拧开水龙头,让水声掩盖住呜咽。
饭桌上,我试探的问起妈妈。
“爸爸工作这么忙吗?过年都不休。”
“理解,工作要紧。”
我低下头,用力咀嚼着嘴里的米饭,却尝不出任何味道,胃里像堵着一块冰。
不能再等了。
假期最后一天,我提前到了医院。
和血液科病区的护士随口闲聊。
“最近忙吧?过年都没法清净。”
“可不是嘛,特别是那几个高危的白血病孩子,治疗不能停。有个叫许愿的小姑娘,才六岁,可怜见的。”
我的心猛地一缩。
“许愿?这名字挺特别。”
“是啊,长得也可爱,她爸也上心,几乎天天来,陪着做治疗,哄着吃药,有时候一守就是一夜。这种爸爸,现在少见了。”
“是啊……”
我轻声附和,喉咙发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