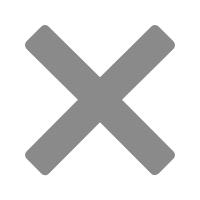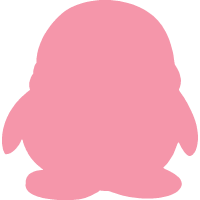2
我偏头躲开,碎屑还是落了我一头一脸。
不疼,但屈辱,我沉默着,没有擦拭。
周浩着急地催促。
“爸,你快劝劝我妈!”
周建国立刻拿出手帕,小心翼翼地为我清理。
“不管怎么样,你们都不能动手,她是我老婆。”
即便闹掰了,父子俩依旧表现得温柔体贴。
他们的克制与风度,反而衬托得我像个歇斯底里的泼妇。
看到周浩急得满头大汗。
周建国的退休老领导重重地叹了口气,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“小苏啊,你这些年为建国操持家务确实辛苦,我们都看在眼里。”
“今天是建国光荣退休的好日子,你就当给我个面子,别闹了行不行?”
“有什么问题,等回家了你们夫妻俩关起门来慢慢说。”
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,用近乎祈求的口吻对我说话。
在场所有人都屏息凝神,觉得我应该会顺着这个台阶下来。
可我面色不变,固执地看着周建国。
“没什么好说的,今天必须签。”
斥责声立刻此起彼伏地朝我涌了过来。
一个跟周建国称兄道弟的车间主任卷起袖子上来拉扯我。
“忘恩负义的东西,要不是老周,你现在还在乡下种地呢,今天我非得替他教训你!”
弟弟死死拽着我的胳膊,压低声音:
“姐,我求你了,你别再闹了!”
“不然我们全家都得被人戳脊梁骨!”
我扯了扯嘴角冷笑。
“随便。”
“今天谁劝都没用,这个婚我离定了。”
周建国擦去眼角的泪花,一把抢过我弟弟手里的协议。
“苏晴,你死了这条心!我不会签的。”
离婚协议被他撕成了碎片。
在飘落的纸屑中,我紧紧注视着周建国,捕捉到一闪而过的慌乱。
“你不签,我就去法院起诉。”
我说完转身就走。
周浩从背后抱住我的腰,不肯松手。
“妈,我爸知道错了,他不该跟你要那笔钱。”
“不就是九百多块钱吗?我出还不行吗?”
“你别因为这个就不要我跟爸了,求你了……”
二十几岁的大男人像个孩子一样苦苦恳求,让在场不少人都红了眼眶。
我用力掰开周浩的手指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楼。
坐上公交车,我无力地看着窗外。
就在这时周建国发来了信息。
我点开聊天框,无意间划到昨天他发的语音。
“晴啊,我算过了,买那只表,还差999块,这笔钱你来出吧。”
“你就当把当年的彩礼退给我,反正现在也不流行要彩礼了,咱们也不能落后。”
我听着这段话,紧绷的身体终于垮了下来,靠在车窗上失声痛哭。
这天晚上,我没有回家。
我来到酒店,想试试那张我从未刷过的卡,却发现手机已经收到一条银行短信。
我和周建国唯一的联名账户被单方面冻结。
说是联名账户,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。
三十年来,我将所有收入都交由周建国打理,他每个月按时取一小部分生活费交到我手上。
说剩下的攒给儿子买房。
我从没留过心眼,他用我的信任,釜底抽薪。
今天的事情闹得整个厂的工友都知道了,群里全是讨论的消息。
“周厂长这辈子就是被她给害了,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几十年,临老了连九百多块钱都都要伸手跟老婆要,真是心酸。”
“别看她一把年纪,平时又衣着朴素,今天穿上礼服,那骚味都快呼我脸上了,臭不要脸。”
“我看她是把厂长那么多年的钱都在外面包小鲜肉了吧。”
“看她儿子眼眶都红了,一把年纪还离婚,这不是给儿子丢人吗?”
我随手退出了群聊,不再理会。
终于做了自己想做的事,这一晚我睡得香甜。
次日我约了赵律师见面。
可能我和周建国知道我一辈子也就认识这么一个律师吧。
我还没进电梯,就被几个人拦住了去路。
为首的是厂办的刘主任,他身后还跟着几名职工代表。
“嫂子,我们代表厂里两千多名职工,来慰问一下您。”
刘主任的话说得客气,但嫌恶的白眼已经翻上了天。
“周厂长跟您一直是厂里的模范夫妻,您有什么想不开的,可以跟组织反映嘛。”
“听说您和供应商老吴走得很近,这其中该不会有什么内情吧?”
“周厂长那套房子是单位分的,您可不能打歪主意。”
他们一唱一和,就是想告诉所有人我吞了周建国一辈子的积蓄在外面偷人。
我懒得与他们废话,正要走,身后却传来周建国疲惫的声音。
“刘主任,你们别这样,这是我们自己的事。”
看到周建国带着儿子周浩赶来,那几位职工代表立刻围了上去。
“老厂长,我们都是为您抱不平!”
周建国满脸愁容地拉住我,语气沉痛。
“阿晴,回家吧,别再让外人看笑话了。”
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
周建国深情包容的表情下,心里的算盘算得比谁都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