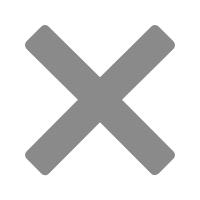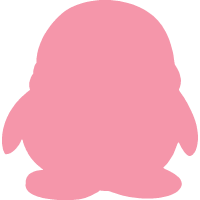2
沈亦臻如往常一样做好了早餐。
三明治烤得金黄,牛奶温得刚好,杯壁印着我的名字缩写——他执行着丈夫的义务,无可指摘。
唯独领口那抹淡绿药膏痕迹,像根细针,扎得我坐立难安。
那是苏蔓专用的牌子。
去年她皮炎发作,我陪她去医院,医生特意提醒过容易沾染且不易清洗。
当时沈亦臻还笑着接话:“蔓蔓这么爱漂亮,可得小心别弄脏新衣服。”
“你领口沾了什么东西?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紧。
他明显一怔,摸向领口的手指蹭到那片绿色时顿了顿,随即扯出个笑:“可能……是蹭到会议室绿植了。”
话音未落,他已下意识将衣领扯向肩侧,目光投向窗外。
我没再追问。
低头灌下那杯牛奶,冰凉的液体没能压下心头的火,反而像一道冰线,直坠到胃里。
我放下杯子,起身拎包:“我去工作室了。”
换鞋时,记忆不受控地翻涌——大学时在咖啡馆,苏蔓总借我的外套,说她怕冷。
那药膏也曾这样蹭在我衣领上,我当时竟觉得,那是友情的印记。
楼下梧桐叶沙沙作响。
我发动车子,抬眼见后视镜里,沈亦臻正站在阳台,身影在晨光里模糊成一团挥之不去的阴翳。
到了工作室,苏蔓正对着电脑。
见我进来她立刻起身,一只手状若无意地将后颈的头发又拢了拢。
“晚晚,生日快乐!”她指尖摩挲着胸前那枚珍珠胸针的底座。
“你看,是不是和你喜欢的那款一模一样?”
我当初要求刻的是“W”。
而那里,此刻嵌着一个小小的“M”。
“挺好看的。”
我移开视线,目光扫过她桌角——我送她的那只保温杯还在原处,杯壁上星星贴纸的边角已然卷曲泛黄。
她曾说要用它天天给我带汤,现在,它安静地立在那里,仿佛一个被遗忘的承诺。
整个上午,我试图专注于屏幕上的线条,心神却总是不自觉地留意着门口的动静。
临近午休,我起身去茶水间,远远便听见里面传来压低的交谈声。
我心下一沉,我放轻脚步。
“胃不好还喝冰的?”
“给你,银耳羹。脖子还没好全,别瞎折腾。”
“亦臻哥……”苏蔓的声音怯怯的,“晚晚她……不会过来吧?”
“放心,我看了眼,她正忙着改图呢。”
那一刻,我才恍然——原来他站在阳台,不是为了目送我,而是在计算我离开的时间,好赶来赴另一场约会。
我退后几步,转身躲进消防通道,冰凉的铁门贴着脊背,我顺着门滑坐在地。
手机在掌中震动,屏幕亮起,是他发来的信息:“老婆,晚上订了旋转餐厅,庆祝纪念日。”
去年今日,他穿越大半个城市,只为买回一块我随口提过的蛋糕。
而此刻,这条精心编辑的短信,与几分钟前他体贴递给苏蔓的羹汤,在眼前重叠交错。
我盯着信息看了很久,手指悬在屏幕上,最终没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