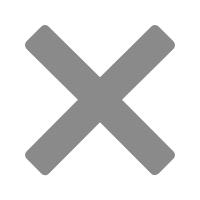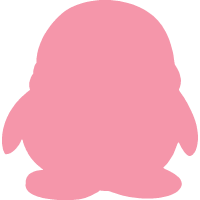2
之后日子平静。沈烬很忙,来后宫次数不多,多是在苏义芸那里,偶尔去别处以示雨露均沾。来我这里,寥寥无几。
每次来,他总带着疲惫。有时问问习惯否,有时说说前朝事。说完,常会沉默,看着窗外或我,眼神复杂。
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歉意,无奈,或许还有未尽的旧情。但这些被皇权朝局包裹,早已变味。
有一次他喝了酒,来我宫里。他拉着我的手,手指发烫。“阿倾,还记得吗?小时候我说要娶你,你说除非我能打赢你。后来我天天练武,终于把你摔地上了。”
我记得。那年我们十二岁,在演武场,他把我撂倒,自己磕破膝盖。我们一起躺在地上看天大笑。
“记得。”我说。
他眼睛亮了一下,又黯下去。“可现在……”他没说下去,用力握了握我的手,松开,转身走了。
那晚之后,他很久没来。
苏义芸倒常邀我去喝茶下棋。她棋艺不错,心静,布局稳。我们话不多,但相处自在。她知道我爱看兵书,有时托人寻孤本给我。她知道我夜里易醒,又给我几种安神香方。
“姐姐气血有亏,旧伤未愈,不能只用安神,还需温养。”她认真递过方子,“这是太医院老太医的家传方子,我用着还好,姐姐试试。”
我接过方子,字迹清秀。“多谢。”
“姐姐不必客气。”她微微一笑,“这宫里真心人少,能说得上话的更少。姐姐不嫌我烦就好。”
怎么会烦。她是唯一不与我谈论沈烬,不计较得失,单纯对我好的人。
深冬时,我旧伤发作,咳得厉害,夜里发热。沈烬派了太医,赏了药材。苏义芸几乎天天来,有时带亲自炖的汤,有时只是坐坐,替我换额上帕子。
“姐姐这伤,是落鹰峡留下的吧?”她一边拧帕子一边问。
我诧异: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陛下有一次提起。”她将凉帕子敷在我额头,动作轻柔,“说那一战极其凶险,姐姐为救被困中军,率轻骑突入,后背中箭,落下病根。”她叹了口气,“陛下说,那次若是姐姐有什么不测,他……”
她停住,没再说。
我闭眼。落鹰峡,那支箭贯穿铠甲,差点伤到心脉。昏迷前,我看到沈烬冲来,脸色惨白,眼里全是恐惧。醒来时,他守在床边,胡子拉碴,紧抓我的手说:“阿倾,以后不准再这样,不准再离开我视线。”
那时的恐惧是真的,情意也是真的。
只是“以后”太长,长到让很多东西变质。
“都过去了。”我说。
苏义芸沉默一会儿,说:“姐姐,值得吗?”
我没回答。值不值得,现在问已无意义。
病好后,我与苏义芸走得更近。这引起微词。有嫔妃议论我巴结皇后,说我失了圣心另寻靠山。也有流言揣测皇后拉拢旧人巩固地位。
这些声音隐约传来,我只当没听见。苏义芸似乎也听说了,一次下棋时,她说:“姐姐,若因为我让你平添烦恼,以后我便少来些。”
我落下一子:“下棋便下棋,想那些做什么。”
她一愣,然后笑了:“姐姐说得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