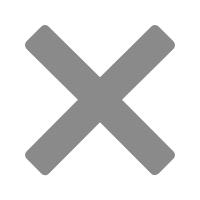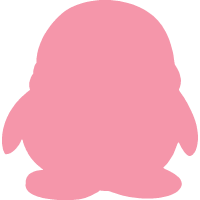3
开春后,边关传来不好消息。北狄部落有异动,小摩擦不断。沈烬越发忙碌,眉头总锁着。
一天夜里,他已歇下,被急报叫起。匆匆离开时,他回头看我一眼,眼神里有我熟悉的、属于战事将起的凝重。
之后气氛明显紧张。朝会频繁,武将出入增多。后宫用度稍减,宴乐皆停。
苏义芸脸上也有忧色。她父亲是文臣,兄长在兵部。她有时低声问我:“姐姐,依你看,这次狄人是骚扰还是……”
我看着庭中抽芽的树木,说:“不像骚扰。像是在等什么。”
她神色更忧:“陛下为此事,好几夜没睡好了。”
我不知该说什么。沈烬的难处我知道,边境安宁没几年,国库经不起大战。朝中武将青黄不接,若真打起来,很吃力。
又过半个月,坏消息来了。北狄联合西羌,集结重兵,突袭天门关。守将轻敌,关隘失守。狄人铁骑南下,连破三城,烧杀抢掠,直逼潼川。
潼川是京师屏障,潼川一破,京城危矣。
朝野震动。主战主和吵成一团。有言迁都南避,有言割地求和,有言死战。沈烬在朝堂上发火,砸了杯子,主和派暂时噤声。
但战事不利。援军匆忙赶去,中埋伏,损兵折将。潼川被围,告急文书一日三传。
恐慌蔓延。物价飞涨,富人南逃。宫里人心惶惶,嫔妃面色惶然。
沈烬肉眼可见地憔悴。他来我宫里一次,什么都没说,只是坐着,手撑着头,背影疲惫。
苏义芸也瘦了。她尽力维持后宫秩序,安抚人心,但眼下乌青遮不住。她来我这里时,常沉默,只是握茶杯,看虚空。
“姐姐,”有一天她忽然问,“如果真到了最坏那步,你会走吗?”
我反问:“你会吗?”
她摇头,笑容惨淡:“我是皇后。国若不在,何来皇后。我会陪陛下到最后。”
她说得平静,但我听出决绝。
“你不会走的,对吗姐姐?”她看着我,“不是因为陛下,是因为潼川后面的百姓,对吗?”
我看着她清澈眼睛,点头。
她笑了,眼里有泪光:“我就知道。”
战况持续恶化。潼川守将苦苦支撑,城破似乎只是时间问题。朝中无人敢再领兵出征,恐惧弥漫。
然后那天傍晚,沈烬来了。
他一个人来,没带随从。穿着常服,有些皱,眼睛布满血丝。手里捧着一套折叠整齐的玄色铠甲,上面放着一柄剑。
是我的“惊澜”剑。
他走进来,将铠甲和剑放在桌上。金属与木桌碰撞,发出闷响。
殿内没点灯,暮色昏沉。他站在昏沉里,看我。
“阿倾。”他声音沙哑,“潼川守不住了。”
我没说话。
“朝中无人可用。”他每个字说得很慢很重,像从胸腔挤出,“去的都败了。剩下的不敢去。”
他向前一步,暮光勾勒他紧绷的下颌。“国库撑不了太久。必须速战速决,击退狄人主力,才能喘息谈后续。”他又向前一步,几乎到我面前,眼睛死死盯着我,“需要一场大胜。一场足以震慑狄人稳住局势的大胜。”
他目光落向铠甲,又移回我脸上,里面翻滚痛苦挣扎恳求,还有孤注一掷的绝望。
“阿倾,只有你能做到。”他声音发颤,“你熟悉狄人战法,你带过潼川的兵,你是唯一可能创造奇迹的人。”
他伸手,似乎想碰我,又在半空停住,握成拳。
“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。”他低头,肩膀垮下,“我知道我负了你,负了从前所有承诺。你要恨我怨我,都是应当的。”
他猛地抬头,眼眶通红:“但阿倾,这不是为了我,不是为了沈家江山!潼川后面是数十万百姓!一旦城破,狄人屠城惨剧又会重演!那些百姓那些活生生的人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