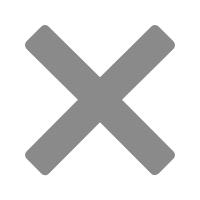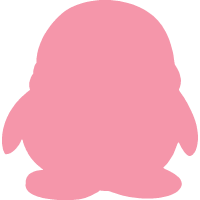-
云开见月明
本书由果悦文化_好看的言情小说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1
成婚八年,系统一直叫我收集夫君的心碎值
可我们举案齐眉,家庭和睦,他有什么可心碎的?
“任务即将失败,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”
系统催促之下,我只得掏出匕首将他的心捣了个稀碎
1
翠儿把药端进房间时,我正在准备年节前的岁飨。
这些年汤药一副副地补,我身子却越来越差。
十年前那场怪病,让京城名医都束手无策。
父母广发告示寻能人义士,盼有人能救我。
直到那个盲眼方士叩响门环。
他空洞的眼神对着我,“小姐这不是病。”
“是魂魄不全,需得请个人回来镇着。”
父母依言派人四处寻访,最后在城南破庙里找到了彼时还是个穷书生的傅怀瑾。
说来也怪,他进府那日,缠绵病榻的我便能坐起身喝下半碗粥。
不出三日,已能下地走动。
一个月后,傅怀瑾收拾行囊主动请辞。
父亲为感激他,将他引荐至骊山书院读书。
可马车刚出城,我便在晨起梳妆时突然呕出血来。
消息传到驿站那日,傅怀瑾调转车头回来了。
我躺在榻上,看见他风尘仆仆地跨进门,胸口郁结难忍的疼痛竟慢慢散了。
后来的一切都顺理成章。
父亲收他做义子,母亲待他视如己出。
及笄礼那日,母亲拉着我的手说:“瑾儿是个靠得住的。”
我俩自然而然结为夫妻。
也是从那时起,我的脑海中多了个叫系统的东西。
“宿主,任务一旦失败,你将被彻底抹除。”
我挥退了翠儿,对着空气轻声道:“你看我这身子,即便你不抹去,我也时日无多了。”
“你不打算再争取一下吗?”系统的声音里竟透出一丝无奈。
我没有回答。
我难道不曾争取过吗?
这些年来,我努力做一个贤妻。
产子那夜我痛了整整七个时辰,他守在门外,不慌不忙赏雪煮茶。
我缠绵病榻时,他衣不解带地照料,可眼中只有不耐,不见担忧。
三年前翰林院走水,父兄殒命,母亲心灰意冷遁入空门,我哭晕在他怀中。
他轻轻拍着我的背,可那心碎值,始终稳稳地停在零上。
他像一尊完美无瑕的玉雕,温润,周全,却没有一丝裂痕。
我的目光落在桌上那碗犹温的药上。
他方才,应是刚从婉娘那里回来吧。
那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事了。
我产后血崩,几乎踏进鬼门关。
弥留之际,十年前那位盲眼方士,竟又诡异地出现了。
他对着我的生辰八字掐算了半晌,灰白的眼睛转向傅怀瑾,“夫人的劫,比十年前更重了。单靠公子一人之气已难以压制,需得寻一个八字与夫人互补的纯阴女子,每月以血为药引,或许能再争一争天命。”
傅怀瑾接过那张写着八字的红纸,只看一眼,脸色骤然一僵
“非此人不可吗?”
方士咧开嘴,露出一个诡异的笑,没有回答。
第二天,婉娘就被一顶小轿接进了府。
取血,煎药,我竟真的从鬼门关爬了回来,只是身子彻底垮了,再离不开汤药。
后来我才知道,婉娘是傅怀瑾的青梅。
我本想将她留在府中,以小姐之礼相待,也算报答。
可傅怀瑾说,婉娘性子孤洁,愿以血相助是出于慈悲,却不愿寄人篱下。
于是,他在城西为她置办了一处清雅小院。
我与傅怀瑾,本始于一场各取所需的“冲喜”。
故而,对于他和婉娘之间究竟是何情谊,我从不深究,也无力深究。
“最近其他世界的攻略者,流行一种死人文学,你要不要试试?”
系统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,我扯了扯嘴角“什么意思?你要提前杀了我?”
“不,是你主动自尽。之后,我会让你的魂魄留在他身边,看着他悔不当初,痛不欲生。等他心碎值满格,我自会让你健康地回来。届时,你们便能拥有真正的圆满。”
真正的圆满?
我望向镜中那个面色蜡黄、眼窝深陷的女人。
早在那场改变一切的大病之前,我的人生,何尝不是圆满的?
我的圆满,本就不在他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