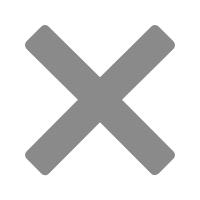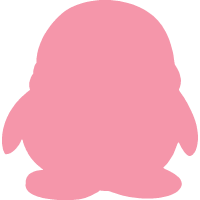2
饮下那碗温热的药汁,我来到书房。
这里我平日极少踏足。
傅怀瑾偏爱在此处点一种清冽的栀子香,我闻了便觉额角闷痛。
强忍着不适整理完账册,一阵熟悉的眩晕猛然袭来。
我眼前发黑,下意识伸手扶向身侧的烛台。
只听得一阵沉闷的机括转动声,靠墙的书架旁,竟悄无声息地滑开一道暗格。
我屏息上前,暗格中并无金银,只静静躺着一张药方和一封摁了红泥的休书。
怪不得系统催促我,再不推进任务,我不但要死了,还要被休了。
把休书烧成灰,又将药方小心誊抄一份。
我寻了个由头出府,直奔城中最大的仁济堂。
坐堂的老大夫捻着胡须,对着方子端详半晌,眉头微蹙。
“夫人,此方平和中正,多是调理气血的寻常药材。说治病药力未免太轻...说吊命却也无甚奇效。敢问是治何症?”
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
回到府中时,天色已近黄昏。
傅怀瑾身边的小厮阿贵垂手禀报:“老爷去了李大人府上诗酒雅集,说晚间不必等他了。”
我点了点头,面上无波无澜。
今夜,与往常无数个夜晚并无不同。
我依旧对着摇曳的烛火,守在房中。
夜渐深,廊下终于传来略显踉跄的脚步声。
门被推开,浓重的酒气先于人涌了进来。
傅怀瑾醉眼朦胧,脚步虚浮。
我如往常般起身,迎上前扶住他的手臂,担忧地问道:“夫君怎么饮了这么多?仔细身子。”
他顺势将大半重量压在我肩上,温热的气息拂过我侧颈。
许是我身上还沾着栀子香,只听他含糊地呢喃着:“婉娘……”
那声音极轻,说罢,他像是骤然清醒了几分。
不着痕迹地拉开些许距离,转而扶住我的胳膊。
语气恢复了平日的疏离:“云江?这么晚了,我可是吵醒你了?”
“没有。”我垂眸,扶着他走向床榻,“夫君快歇下吧。”
替他除去外袍鞋袜,看着他阖上眼,呼吸逐渐变得绵长安稳。
我站在床边,静静地看了他许久。
然后,从袖中缓缓抽出那柄早已备好的刺骨匕首。
不再犹豫,精准地没入他胸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