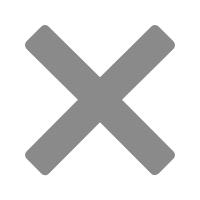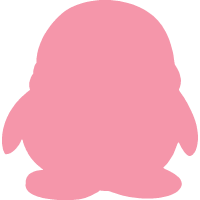2
我瘫坐在凳子上,望着他决绝的背影。
冷风裹挟着雪花扑到我的脸上,冰凉一片。
像极了父兄战死时的那场大雪。
护国公府父子三人皆以身殉国。
消息传来,祖母便一头栽了过去。
起灵那日,母亲也终受不住,一头磕在父亲的棺前随他而去。
天地一片缟素。
偌大的护国公府只剩我一个孤女。
沈松年来寻我时,三尺白绫悬梁,我恰踢了脚下的矮凳。
他疯了一般冲进来,将我抱下。
哭着说:“阿鸾,别怕,以后我护着你。”
他为我父兄抬棺,陪着我一起守孝三年。
一点点将我心中的死志消融。
他说待孝期满,便与我成婚,我们会有自己的家。
他说我可以永远像父兄在时那般骄纵,做这上京最璀璨的明珠。
他说他会永远哄着我,让着我。
言犹在耳,不过三载,他却说他累了。
我急火攻心,呕出一口淤血,吓得翠儿急忙去请大夫。
号完脉后,大夫边收拾东西边道:“夫人怀孕已三月有余,切不可再如此大动情绪。”
“什么?”我心中大喜。
这个孩子我与沈松年已盼了三年。
我相信他若知道心中定然也是欢喜的。
那柳娘,不过是他迷了心智。
一个倒夜香的瘸腿寡妇,如何配得芝兰玉树上昌平侯?
不过是他恼了我平时太过任性。
第二日,我挑沈松年上值的时间,乘着马车来到了西市牛尾巷。
巷子逼仄,马车进不去,只得停在外面。
我看着绣鞋上粘的污渍,心中不由得烦闷。
我更加确信沈松年不会过得惯这种日子。
“这里是白银千两。离开这里,这些银钱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”
我将银票推过去。
她低着头,在缝一件月白色的里衣。
是沈松年的,衣摆处还有我亲手绣上去的松树花样。
发黄的麻线,粗劣的针脚。
很明显并不合适。
但我在沈松年的其他衣服上也见过。
他还诓我说是不想麻烦我自己缝补的。
她咬断麻线,红了眼眶,将衣服叠整齐。
却看也未看桌上的银票。
“夫人不必如此,我这就离开。”
她转身拖着残腿开始收拾行囊。
我心里忽然堵得发慌,扶着翠儿的手离开。
嘱咐车夫去寻一辆马车送一送她。
谁知,当晚,沈松年一脚踹开我的房门,满脸怒气,抓着我的手腕质问。
“叶青鸾,我那般恳切地求你放过柳娘,你竟还能下得去毒手,你个毒妇!”
他说着就大力将我往床下拖。
翠儿拼死过来抱住我,跪在地上“咚咚”地磕头。
“侯爷息怒!”
“夫人怀了身子,经不起您这样折腾!”
他闻言,停了动作,怔怔地望着我。
“原来你也怀孕了。”
“怪不得……”
沈松年离开后,我才得知柳娘离开时乘坐的那辆马车出了城便坠湖了。
柳娘得人救助,活了下来。
但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……
我僵在床上,脑中一片空白。
不知是为这场意外,还是为柳娘竟怀了沈松年的孩子……
我知这件事沈松年定然对我误会颇深,我有心解释,却寻不到机会。
半月后,沈松年终于归家。
他似乎很是疲惫。
满面风尘,半跪在我的床前。
我腹中孩儿已四月有余,小腹微微地隆起。
他轻抚着,露出久违的微笑。
我以为,我终于等来了他的回心转意。
他也似乎真的变回了以前那个爱着我、捧着我的沈松年。
他不再提柳娘,我也闭口不言。
我想一切都已过去,我和沈松年的日子终究还会和以前一样恩爱甜蜜。
转眼间,孩子已快足六月,大夫嘱咐我少食多动。
沈松年却似没听到一般,每日流水般地补品喂着我,平日也不允许我下床走动。
我只当他是担心孩子。
却不想,一日,我喝完他亲手喂的安胎药,忽然腹痛如绞。
我疼得大汗淋淋,腿间有温热流出。
我大惊,抓着他的手。
“夫君!”
他却甩开我,后退半步。
满脸冷漠。
“那日柳娘也是如此痛的。”
“叶青鸾,我要你比柳娘更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