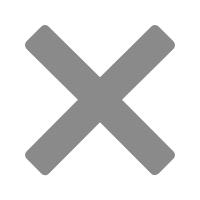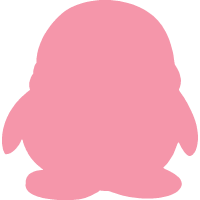2
朝野上下掀起轩然大波,谢允却将人牢牢地护在东宫。
彼时我风寒未愈,收到父亲密信。
也只能拖着病体去劝他。
谢允的书房内地龙烧得滚烫。
那新封的良娣只穿了身薄如蝉翼的纱衣,娇笑着依偎在谢允怀里。
我移开眼,逼自己忽视眼前活色生香的情景。
谢允却先一步开口:“锦鸳,我知你受家族掣肘,不得不来劝我。回去告诉裴相,若是再阻拦,日后你的皇后之位就难说了。”
他神情冰冷,眼底满是凉薄的威胁。
我张了张嘴,话却哽在喉间。
想起当年新婚,面如冠玉的少年掀起我的盖头。
郑重其事地对我许诺:“京城贵女里,唯有锦鸳不嫌我出身低微。从今往后,锦鸳便是我的妻子,我定会珍之爱之。”
时移世易,如今大皇子病重,其余皇子不成器。
谢允已是无可动摇的储君。
他铁了心要给心上人一个名分。
我又能说什么呢?
怨他毁诺?还是怨他变心?
我咽下满心苦涩,仍旧劝道:“殿下初当储君,若是堂堂正正纳个良家女子自然无可指摘。可这女子,出身实在不堪……”
谢允轻抚着怀中女子的脊背,高高在上地反问:“出身不堪,认在你家中做妹妹不就好了?”
“河东裴氏的名声,还不够堵住悠悠众口吗?”
我猛地抬起头,不敢相信这么荒谬的话竟是从谢允嘴里说出来。
原来他打的是这主意。
顶着河东裴氏的名头,的确无人再敢质疑这女子的出身。
可这是何其大的羞辱?
若是认下这个青楼出身的妹妹,让我裴家其余的女儿如何嫁人?
父兄在朝为官,又让他们在朝中如何做人?
这些谢允怎么会不知道。
他不过是恼怒父亲屡屡上书反对他纳妾,才故意羞辱裴家。
我又急又怒,多年来第一次对谢允生出悔恨。
这一刻,我才意识到谢允从来不是那个与我琴瑟和鸣的夫君。
他是未来的天子。
生杀允夺不过是一念之间,羞辱都算是格外开恩了。
我心神震荡,回到宫里就生了场大病。
这一病,却诊出了喜脉。
再醒来时,谢允守在床边。
他满眼欢喜,笑着埋怨我:“怎么有了身孕还未察觉?若是出了事,孤怕是悔之晚矣。”
见我闭着眼不愿看他。
谢允叹了口气,又说:“你安心养胎,至于娇娇的事,孤已让人对外说她是平远侯走失多年的女儿。”
“鸳儿,你爹他上朝总骂娇娇红颜祸水。孤只是恼他才说了气话,孤的妻子只有你。”
娇娇便是他带回来的那女子。
我捏紧被子,问出的话极轻:“那若是殿下日后也恼了我呢?”
谢允答不出来。
他明白了我的惊惶,却没法给我任何许诺。
许诺什么呢?
永远不会恼我?还是永远让我稳坐太子妃的位子。
他是未来的帝王,这些他都做不到。
谢允仓皇甩袖离去,背影逃也似的。
我伸手抚上小腹,太医来时我就醒了。
正好听见他说,这孩子已经有三个月了,再过些日子恐怕便能感受到胎动了。
但我却仿佛能感受到皮肉之下属于另一个生命的磅礴心跳。
我怆然泪下,满心不舍。
为何偏偏是在这时候?
偏偏在我对谢允彻底失望的时刻,让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