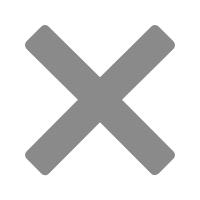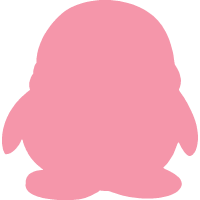2
听着妈妈话,我呼吸一滞。
借口打水,逃似得奔出产房。
从妈妈推搡的动作里,小小的我敏锐地察觉到妈妈最爱听我说想要个弟弟。
年幼的我为了讨妈妈欢心,开始时不时地提起关于弟弟的话题。
妈妈每次一听,就眉开眼笑的奖励我一颗糖果:
「好孩子,就要这么说。」
直到初中时,妈妈捏着我的成绩单,嫌恶地用指尖狠狠戳着我的额头:
「林文婷啊林文婷,你考个第二名你还好意思回家?」
「你这个样子,以后怎么给你弟弟做榜样?」
她的话激起我叛逆期的反骨,我梗着脖子冲妈妈大喊:
「你总用弟弟来压我,可我根本就没有弟弟!」
妈妈双眼瞬间猩红,她大步向前冲上来捏住我的下巴,抓起水壶就往我嘴里灌:
「洗嘴!重说!」
我奋力扭动着身体却不敌妈妈的桎梏,水撒得到处都是,呛得我近乎窒息。
直到水壶空了,我抓住空隙,哭嚎着:
「弟弟,我要弟弟!」
妈妈才松开我,如释重负地露出一个笑。
她施舍般把劫后余生低声啜泣的我揽进怀里,轻轻拍打:
「以后别乱讲,等妈妈生出弟弟就好了。」
「从今天开始,你每天要跪在祠堂前扇自己五百个巴掌,弥补你今天的失言。」
我倚在妈妈的怀里止不住地颤抖,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惊惧笼罩着我。
妈妈见我不出声,面露愠色,把我从她怀中撕开,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:
「你哑巴了?」
我这才反应过来,惶恐地连连点头,生怕点慢了妈妈接着教训我。
自那天起,我成了家里的「盼弟石」。
妈妈每天监督我,盯着我边抽自己巴掌边对着祖宗许愿:
「我林文婷独女寂寞,求列祖列宗给我一个弟弟,给我一个直起腰杆的底气。」
打满五百个巴掌才肯放我去上学。
因为我的脸总是又红又肿,「猴屁股」绰号跟随了我整个学生时代。
壶中溢出的开水扯回我的意识,我条件反射地松开把手。
暖水壶「哐当」在地上炸开,沸水劈头盖脸地泼了我一身。
皮肤瞬间红了一片。
手机铃声响起,妈妈不耐烦地催促:
「打个水磨磨蹭蹭这么久,你在外面偷人啊?」
「怪不得是读书人,精得很。听到让你赎罪就跑路,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你也永远欠你弟弟的,懂吗?」
我心头一紧,酸涩翻涌着泛上来。
高考后,爸爸死活不让我接着念,是妈妈在旁劝和:
「姐姐是个大学生,以后才能教好弟弟。」
爸爸才松了口。
他们为我报了一所本地的大专,可我成绩优异,明明能读更好的学校。
我背着爸妈把志愿改成首都的 985。
录取通知书送到的当天,爸妈才知道这件事。
爸爸怒不可遏,拿着晾衣杆狠厉地抽打着我和妈妈。
妈妈已经怀孕三个月,被爸爸打得当场流产。
那是一个已经成型的男胎。
我永远也忘不了妈妈躺在病床上哀怨的眼神。
她猛地抓起床边的病历垫板砸向我,语气中满是恨之入骨的笃定:
「林文婷,我对你这么好,你却杀了你弟弟,你这个杀人犯!」
「你怎么不去死?该死的是你!」
垫板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幼时头磕到水泥地的伤口上。
早已留疤的伤口再次喷涌出鲜血。
温热的液体顺着脖颈留到我的手上,时刻提醒我,我对不起爸妈。
可我做错了什么呢?
我不过是想去更好的学校,看更大的世界。
为什么仅仅是这样,也是罪?
我不明白。
尽管妈妈的咒骂是我挥之不去的噩梦,但我仍然惶恐地上贡每一笔工资,希望能弥补一点妈妈的丧子之痛。
然而,时至今日我才明白,就算我出类拔萃、为这个家一心付出,在妈妈眼里还是比不过生来就带把。
我省吃俭用贴补家里,在她眼里不过是我精明的体现。
她根本不爱我。
不对等的感情没有继续的必要,即便是血脉相承的亲人。
这份亲情,我不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