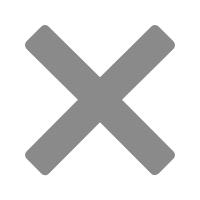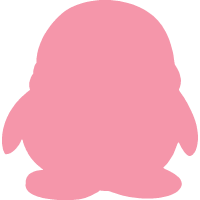4
“你给他喝了什么?!”
她抢过我的水杯,闻了闻,然后狠狠摔在地上,玻璃碎片四溅。
“我只是倒水给自己喝。”
“撒谎!你想毒死我儿子!我知道你恨他!”她抓住我的头发,把我拖到客厅。
头皮传来撕裂的痛感,我尖叫起来。
爸爸被吵醒,出来看到这一幕:“慧芳!放手!”
但她不听,开始用脚踹我的腹部。
我蜷缩起来,剧痛让我无法呼吸。
爸爸终于上前拉住她。
“她是恶魔!她想害我的孩子!”她尖叫着,泪水横流。
爸爸费力地把她拉回卧室,锁上门。
我躺在冰凉的地板上,腹部一阵阵痉挛的疼痛,嘴里有血腥味。
天花板的灯刺眼,我闭上眼睛,眼泪从眼角滑落。
不知过了多久,卧室门开了。
妈妈走出来,脚步虚浮。
她跪在我身边,颤抖的手抚摸我的脸:“小欣,我的小欣,妈妈做了什么。”
她看到我嘴角的血,突然崩溃大哭,把我搂进怀里:“对不起,妈妈不是人!你打妈妈,打回来。”
我摇头,说不出话。
那天晚上,她坚持要给我上药。
撩起我的衣服,看到腹部大片的瘀青,她倒抽一口冷气,手抖得几乎拿不住药膏。
我反而安慰她:“没事妈,会好的,你只是生病了。”
她抬头看我,眼神复杂,有痛苦,有愧疚,还有一种我那时看不懂的情绪。
她说,声音很轻:“对,妈妈会好的。”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那个雨夜。
我被一阵剧烈的腹痛惊醒。
白天妈妈踹了我肚子好几脚。
我起身想去客厅找止痛药,经过主卧时,听见里面传来低语。
门虚掩着,透出一线光。
我本能地停下脚步。
“你还要这样到什么时候?”是爸爸的声音,带着不寻常的疲惫。
“小欣身上已经没一块好皮了,昨天班主任又打电话来问,我差点编不下去。”
我心下微酸,贴在墙边,屏住呼吸。
“哼,现在不把她训成小宝的奴隶,将来心野了就不好管教了。”
妈妈的声音清晰,没有丝毫病态:“女儿终究是别人家的人,得让她从小就知道,弟弟才是这个家的中心,等她习惯了逆来顺受,以后嫁人了,在婆家也能站稳脚跟。”
这番话如此平静,如此理性。
像在讨论家务安排,而不是持续两年的虐待。
“可是她毕竟才十四岁,慧芳,你看看她背上的伤。”爸爸的声音里有一丝动摇。
“伤会好的!心理的驯化才是关键!”
妈妈的声音陡然严厉:“你现在心软了?想想我们当初为什么这么做!想想小宝的未来!他需要一个人全心全意照顾他,小欣现在吃点苦,以后就知道本分了,难道你想让她像那些独生女一样娇纵,将来不管弟弟?”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,小欣毕竟是我们一手带大的啊。”
“那是什么意思?医生说了,产后失忆症一般不会超过一年,我已经装得够累了!要不是为了彻底磨掉她的棱角,我何必天天演戏?”
演戏。
这两个字像针刺进我的心脏。
“医生说你这病装不了多久了。”爸爸叹气:“她学校老师已经开始怀疑了。”
“够了,等她习惯了逆来顺受,知道反抗也没用,到时候病好了也无所谓,反倒会感激我好起来,虐待产生忠诚。”
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崩塌。
我扶着墙,才没让自己倒下。
我蹑手蹑脚回到房间,锁上门,把脸埋进枕头无声哭泣。
那一夜,我第一次想到了死。
如果活着意味着每天被最亲的人算计和伤害,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?
但我最终没有。
第二天早上,妈妈又发病了。
早餐时,她突然打翻我面前的牛奶,玻璃杯碎了一地。
“你想毒死我儿子!”她尖叫道,指着洒在地上的牛奶。
我静静地看着她表演,不再试图解释。
爸爸照例出来打圆场:“小欣,快收拾一下,妈妈不是故意的。”
“我是故意的!”妈妈站起来,走向我:“我告诉你,离我儿子远点!”
她扬起手,我这次没有闪躲。
巴掌落下时,我直视她的眼睛,捕捉到那一闪而过的得意。
原来,母爱真的可以伪装。
“看什么看?!”她又是一巴掌。
“慧芳,够了。”爸爸拉住她:“小欣还要上学。”
妈妈冷哼了几声,不再看我。
我沉默着走出家门。
即使同学问我,老师问我,我都闭口不提。
我拿着爸爸偶尔给我的一块钱买了个热鸡蛋敷脸。
回去的时候,弟弟看见了我。
他的大门敞开,要我手上的鸡蛋。
弟弟已经学会吐出几句话了,他的眼神很澄澈,我警惕观察了一下周围,还是心软把鸡蛋递了过去。
弟弟是无辜的,他还只是个小孩。
他握着鸡蛋,没握住,鸡蛋滚到书架下,他用手指着:“姐姐,蛋!”
我柔和地笑了笑。
抽屉也没关上,我抬眼,看到一张不属于我们家人的全家福。
那里有爸爸,有另外一个女人。
还有爷爷奶奶。
我脑子瞬间略过很多想法。
我看向弟弟,弟弟跟我长得并不像。
跟妈妈也不太像,更多的是像爸爸。
可我们一家都是自来卷,弟弟的头发却黑直。
他住保温箱的时候,抽过血。
妈妈睡得迷迷糊糊,我跑过去找护士。
看到弟弟的出生证明,是o型血。
年幼的我不知道,爸妈都是AB型,怎么能生出来o型血的孩子?
我拿出全家福,弟弟反而眼前一亮。
指着那个陌生女人,叫了一声:“妈妈。”
我警铃大作。
更多的谜团让我慌不择路地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