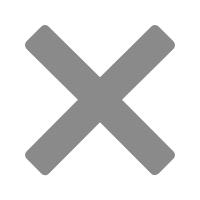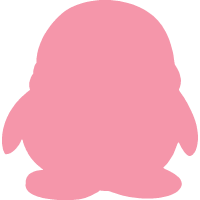3
我拍着她的背。
我相信她。
我必须相信她,母亲的爱是无法作假的,她只是病了。
爸爸带她看过三个医生,诊断大同小异:产后应激障碍导致的短暂性失忆症,可能伴随被害妄想。
每个医生都这样安慰:“会好的,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。”
但爸爸的耐心很快变成了默许。
当妈妈第一次真正打我时,他只是站在一旁,嘴唇动了动,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那天弟弟哭闹不止,妈妈怎么哄都没用。
我做完作业出来,小心地说:“妈妈,要不我试试?”
她猛地抬头,眼神瞬间变得凶狠:“你想干什么?”
她抱紧弟弟后退一步,仿佛我是十恶不赦的坏人。
我一直解释:“我只是想帮忙。”
“帮忙?你是想把他弄哭然后显得我照顾不好是不是?”
她的声音尖利起来:“你一直嫉妒他,我知道!”
“我没有,妈…”
“闭嘴!”她冲过来,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
那一巴掌很重。
清脆的声音在客厅回响,我们都愣住了。
我的脸颊火辣辣地疼,更多的是震惊。
妈妈的手停在半空,颤抖着。
爸爸从报纸后抬起头,看了我们一眼,嘴唇动了动,最终只是说:“慧芳,你冷静点。”
“她想害小宝,她是谁?”妈妈的声音开始不稳,眼神涣散。
“小欣,你先回房间。”爸爸叹了一口气,声音疲惫。
我捂着脸回到房间,关上门,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。
脸上不疼,疼的是别的地方,从心脏开始,流向四肢。
门外传来妈妈的啜泣和爸爸的安抚声。
几分钟后,敲门声响起。
“小欣,开开门。”
是妈妈,她声音恢复了温柔。
我打开门,她眼睛红肿,伸手想摸我的脸,我下意识地躲开了。
她的手僵在半空,泪水又涌出来:“对不起,妈妈又控制不住了,你疼不疼?”
看着她哭,我的心被她哭软。
“不疼,妈妈。”
她把我搂进怀里,这次我没有躲。
她的怀抱还是记忆中那样温暖,带着淡淡的洗衣液香味。
“妈妈会好的,医生说了,会好的。”她在我耳边喃喃,不知是在安慰我还是安慰自己。
从那以后,暴力的频率和程度逐渐升级。
从推搡到扇耳光,从踢小腿到踹腹部。
每次施暴都有个固定的模式。
先是发病,对我实施暴力。
然后短暂清醒,哭着道歉。
最后是拥抱和承诺。
我相信了这个循环。
因为清醒时的她,太像我记忆中的妈妈了。
爸爸偶尔会拍拍我的头,眼神复杂:“妈妈生病了,你要体谅。”
我点点头,把新添的瘀青用长袖遮住,笑着帮妈妈做家务。
夏天来临,长袖衣服显得突兀,有次体育课换衣服时,同学看到我手臂上的伤痕,惊讶地问:“小欣,你手上怎么了?”
我不敢说,快速套上T恤,笑着岔开话题。
但有些伤是藏不住的。
脸上的巴掌印,即使消了肿,也会留下淡淡的红痕。
有次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,委婉地问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。
我说妈妈生病了,有时会控制不住情绪。
她关切地看着我:“需要老师求助相关部门吗?”
我急切地摇头。
我不能让外人介入,那会伤害妈妈,也会让爸爸难堪。
我们是家人,家人之间的问题要自己解决。
暴力最严重的一次,是我初二期末考试前一天。我在房间复习到深夜,口渴出来倒水。
经过主卧时,弟弟突然哭起来。妈妈冲出来,看到我拿着水杯站在走廊,瞬间暴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