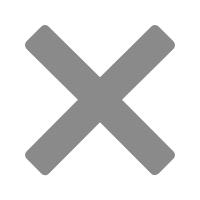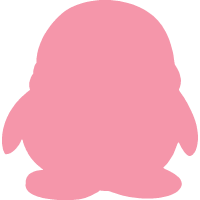3
邻居张叔叔实在看不下去了,冲上来一把拽住妈妈的胳膊。
“素琴!你疯了!安安都这样了!”
妈妈甩开他,力气大得惊人。
“滚开!我在教育孩子!谁也别插手!”
她红着眼,胸口剧烈起伏,手指颤抖着指着地上的我。
“你们不知道,她最会偷懒了。”
“只有99分,全校第一有什么用?那一分才是关键!”
“那一分不拿回来,以后怎么跟人竞争?怎么过独木桥?”
她一边说,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被撕碎、又用透明胶带粘得歪七扭八的试卷。
那上面全是黑灰,胶带都快化了。
她蹲下来,强行要把试卷塞进我那只被烧得黑紫的手里。
“拿着!起来给我重做一遍!”
“错题本我都给你准备好了,今天不做完这一张,晚饭别想吃!”
我的手僵硬得像铁钳。
手指紧紧攥着拳头,那是为了护住书包里的东西。
她掰不开我的手指。
“松手!听到没有!跟妈倔是吧?”
她用力掰,指甲抠进我烧焦的皮肉里。
周围的消防员终于反应过来,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冲上来想拉开她。
“这位家属,请冷静!伤者需要急救!”
“急救个屁!”
妈妈回头冲他们吐了一口唾沫。
“她就是想偷懒!就是想睡觉!”
“在这个家,只要有一口气在,就得给我学!”
“就算是死,也得把卷子做完了再死!”
她挣脱不开消防员的阻拦,转身冲向厨房。
那里还有水。
她接了满满一盆冷水,哗啦一声,狠狠泼在我的脸上。
“给我醒醒!别在这给我演尸体!”
黑灰被冷水冲刷下来。
露出我那张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。
眼睛紧闭,嘴唇发紫,死气沉沉。
水顺着我的鼻腔流进去,灌进喉咙。
往常这时候,我早就跳起来咳嗽了。
可现在,没有任何反应。
水珠静静地挂在我的睫毛上,像永远不会落下的泪。
妈妈的手明显抖了一下。
她愣了一秒,随即脸上又浮现出那种神经质的笑。
“演得真像啊,陈安安。”
“奥斯卡欠你个奖杯是不是?”
“行,你能忍是吧?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!”
她冲上来掐我的人中。
指甲深深陷进皮肉里,掐出了血印,甚至掐破了皮。
我依然一动不动。
就像一个破败的布娃娃,任由她摆布。
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,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厌恶。
他们看妈妈的眼神,不再是看一个严厉的母亲,而是看一个疯子。
妈妈却感觉不到。
她凑到我耳边,用了她往常最管用的杀手锏,声音阴测测的:
“陈安安,再不起来,明天的补习班我就退了。”
“那五千块钱,我拿去喂狗也不给你花!”
“你要是敢让我白花钱,我就死给你看!”
这是她以前百试百灵的咒语。
只要一说死,我就算病得再重也会爬起来做题。
因为我怕她死。
我怕没有妈妈。
可这次,那个“如果不起来就一起死”的咒语,失效了。
妈。
钱留着吧。
喂狗挺好的,狗会冲你摇尾巴。
我只会让你生气。
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。
声音由远及近,刺破了小区的宁静。
急救医生提着箱子冲上楼,满头大汗推开围观的人群。
“让开!都让开!伤者在哪?”
医生看到地上的我,脸一沉。
他蹲下来,伸手去摸我的颈动脉。
没有跳动。
他又拿出听诊器,贴上我满是烟灰的胸口。
在那里的心脏,曾经因为考试少一分而狂跳,因为妈妈的脚步声而紧缩。
现在,它终于安静了。
医生皱着眉,翻开我的眼皮,拿手电筒照了一下。
瞳孔散大,对光反射消失。
医生叹了口气,看了看手表,站起身摇摇头:
“瞳孔散大,无生命体征,死亡时间大约一小时前。”
“没救了,通知殡仪馆吧。”
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,像一道惊雷,炸在狭窄的楼道里。
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除了妈妈。
“放屁!”
一声尖利的咆哮爆发出来。
妈妈像一颗出膛的炮弹,扑上来撕扯医生的白大褂。
“你胡说什么!你这种庸医!”
“她就是睡着了!她昨晚熬夜刷题太累了!”
“她才十七岁!怎么可能死!你再敢咒我女儿,我撕烂你的嘴!”
她疯狂地抓挠医生的脸,两个警察赶紧冲上来,强行控制住她。
“这位女士!请你冷静!”
警察将她按在乌黑的墙壁上。
妈妈的脸贴着冰冷粗糙的墙面,因为用力挣扎而充血涨红。
她的视线,被迫正对着地板上的我。
刚才那一盆水冲刷过后,我的手从蜷缩的状态垂落下来。
那只手,正好对着她的脸。
指尖被高温烧化了,皮肤焦黑卷曲,露出了里面森森的白骨。
那是握笔的手。
那是帮她洗碗的手。
那是无数次想要去牵她,却被她嫌弃有汗甩开的手。
这一刻,她终于看清了。
那不是睡着。
活人的手,不会露出骨头。
“安……安安?”
她的声音突然轻了下来,轻得像蚊子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