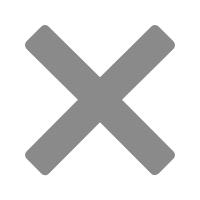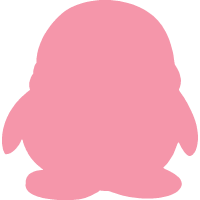2
岭南的日子也很苦。
但那时的沈嘉彦会特意写藏头诗作弄我,会攒钱给我买银梳,还会同我诵诗作词。
直到我瘴毒入体,寒热昏迷。
大夫说,时日无多。
阿婆找到归乡的老御医,打听到能缓瘴毒十年的药参。
可家里早已经没钱买药了。
我休克假死那晚,沈嘉彦哭着给自己熬了碗断肠草。
阿婆拿出王家的信拦住了他。
他放下恩怨,回王韫的第一封信是给我求药。
用王家寄来的第一笔钱是为我求医。
渐渐地,王韫的来信越来越多。
我醒来后,阿婆哭着求我:
「菱丫头,阿婆就只剩一个孙子了。」
我们瞒着沈嘉彦,让他以为这毒能缓一辈子。
药参很贵,沈嘉彦没日没夜地替人抄书到手抖。
我偷偷绣了一张又一张帕子。
加起来都抵不过王韫随手寄来的一袋银钱。
沈嘉彦盯着那袋银子,连日来绷紧的脊背一松,笑得如释重负。
那一瞬的心慌和羞愧,让我口不择言:
「其实御医也说过,用便宜些的参也能活。」
他心疼地摸我的头:
「那怎么行,我们菱丫头要喝最好的药。」
其实只活十天就好,他就不用这么累。
……也不会再回王韫的信了。
岭南车马慢,他回了一封又一封。
病中多思,他每次提笔写信,我都在想:
他会不会也作了藏头诗作弄王姑娘?
信里会夹带着银梳吗?
怪沈嘉彦实在笨拙。
也怪我眼神太好。
信里不是银梳,是翡翠簪子。
我嘲讽他是软骨头,嘴里的话刻薄又难听:
「你恨王韫与你退亲,骂王家无情无义,如今上赶着送簪定情,这就是你沈嘉彦的风骨,不过是趋炎附势的小人。」
沈嘉彦把信纸捏起褶皱,言语如刀:
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?阿韫寄来的钱是救你的命,我回礼感谢合情合理,你袁菱有风骨,那就别喝我熬的药!」
话说得太重,他背过身去不敢看我。
我却瞪着他,不敢眨眼,怕眼泪掉下来。
是我承了王韫的恩惠,所以无理取闹的是我,污蔑他们清白的也是我。
……
去广陵的船还没来。
王韫先递了拜帖来。
我想也不想地回绝了。
她那粉黛未施的芙蓉面,我总要涂脂抹粉许久。
沈嘉彦替我回帖同意了,劝我:
「阿韫想来看望是担心你,你就露个面宽宽她的心。」
我没有去见王韫。
沈嘉彦催人来请不成,最后只好自己来。
「你是沈家的女主人,合该她来看你,但屋子里病气重,过给贵客就不好了。」
从前听到这话,我定然高兴地描眉点唇,硬撑着去前院接待她。
如今却只觉得悲凉。
我们僵持许久,王韫自己找了过来。
少女脚步轻盈,粉衣娇嫩。
而屋里又苦又闷,我难堪地捏紧袖口,闻到了自己身上久病的腐朽。
王韫第一次见我没有妆容遮掩的憔悴。
「菱姐姐,你怎如此作贱自己,累得嘉彦哥日日忧心。」
我勉强笑笑。
她捏着帕子遮住口鼻,要哭不哭地说:
「自我和离归家,日子便不好过,嘉彦哥想帮我又怕我要强,便花钱请我写诗赋。」
「菱姐姐要怪就怪阿韫吧。」
原来是沈嘉彦强买强卖啊。
我再挂不住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