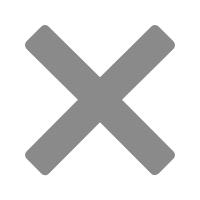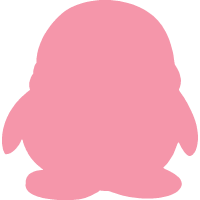3
沈嘉彦把窗支开了条缝,不着痕迹地换了口气后,连忙安抚她:
「怎会怪你?阿菱能活下来本就该谢你。」
我垂眸不语,王韫委屈地红了眼:
「菱姐姐不说话,心里肯定恨死我了……」
「阿菱不怪你,她是在等我倒茶,想以茶代酒谢你呢。」
他将热茶放进我手心,示意我出声附和。
茶解药性,他从不让我喝,只许我拿着暖手。
丝丝缕缕的寒风吹得人发冷,我噙着笑将茶缓缓地倒在地上。
每年上坟我都这样敬过酒。
王韫呼吸一窒,失态地面目狰狞。
沈嘉彦伸手打掉茶杯,眼神阴沉地像是要吃人。
而我人之将死,其言也不善:
「谢她什么?」
「谢她一个弃妇随意插手夫妻间的矛盾?还是谢她故意来戳我的心?」
「王娘子,我们彼此不喜,往后不用假惺惺地上门看望。」
沈嘉彦没有同我争吵,只是冷了我许久。
自那日受了寒,我便病得昏昏沉沉。
直到去广陵的船靠岸了。
阿婆才急着给好几日没回家的沈嘉彦传话。
他匆匆赶回来,焦急化作不耐:
「你气色甚好,生得哪门子病?别又旧病重提。」
我摸了摸烧得通红的双颊,鼻音厚重:
「阿婆说你应了她,要送我去广陵休养。」
他按压眉心,不耐至极:
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少事要忙,没有大病就别乱折腾好吗?」
我心里狠狠一窒,脑袋却晕乎乎地点头。
我过于乖顺,反而让他有些懊恼:
「你再等等,过些时候我一定陪你去广陵。」
没等我说话,王韫的人又上门来找他。
夫妻四载,这大概是最后一面。
「沈嘉彦……」
他头疼地解释:
「你别又多想,阿韫要强,定是难事才会寻我。」
我咽下没说出口的告别,淡淡地嗯了声。
他匆匆地向王家奔去。
我烧得浑身无力,是阿婆让人抬上船去的。
阿婆打包的行李里没有药,大概我确实不需要了。
我咳得厉害,扰得隔壁一连敲了三次门。
「家中女眷娇弱喜静,某想出钱请夫人换一间房。」
门外的声音意外的耳熟。
我开了门,和沈嘉彦面面相觑。
「阿菱——」
他脸上的笑瞬间僵住。
鲜红从我苍白的嘴角溢出,我明知故问:
「郎君口中的女眷是谁?」
他嘴唇微微颤抖:
「我为何不知你的咳疾如此重?快让大夫来瞧瞧。」
我在他面前咳过两次血。
彼时我们正因王韫拌嘴,我也负气说过自己命不久矣的真相。
可看到他哭红的眼,便只敢骗他是咬破了舌头故意吓他。
阿婆得知后找借口让我们分房而居。
他不知道我咳血,盗汗,失眠心悸……更不知道我就要死了。
他呼吸凝重,袖袍下的手都在发抖,此刻的担心毫不作假。
可当我认出他身后的随行大夫后,病态苍白的脸近乎透明。
茯苓堂的廖大夫,专医妇人孕事。
「是王韫有孕了吗?我该恭喜你,喜得外室子。」
我弯下眉眼想笑,却似在哭。
隔壁有东西扔了个响,是王韫听到了在发脾气。
沈嘉彦脸色变换,好像我占了多大的便宜:
「不是外室子,阿韫愿意把孩子记在你名下。」
他低声哄我:
「先让大夫看看你的咳疾,也别在这吵行吗?」
「阿韫是在替你受生育之苦……算了,还是我陪你换一间房吧。」
我笑了,眼眶酸热。
「沈嘉彦,我们和离吧。」
说出口的瞬间,整个人都松快了。
沈嘉彦怔在原地,恼怒里带着几分慌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