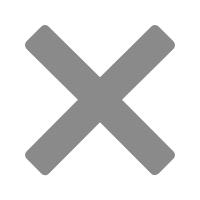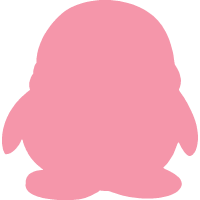2
我被关起来了。
爹把我和刚出生三天的弟弟锁在柴房里。
弟弟饿得哇哇大哭,那哭声像猫叫一样微弱,听得我心如刀绞。
家里没有奶粉,娘走得急,什么都没留下。
“爹!弟弟饿了!你让他喝口米汤也行啊!”
我拼命拍打着柴房的门。
门外静悄悄的,只有熬药的咕嘟声和中药味。
过了很久,门缝底下塞进来半碗米汤。
我赶紧端起来喂弟弟,一边喂一边掉眼泪。
这原本是个虽然穷但很温馨的家啊,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鬼窟?
入夜,家里静得可怕。
弟弟哭累了,睡了过去。
我缩在柴草堆里,又冷又怕,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剪刀。
那是娘生前用的,现在却成了我唯一的防身武器。
凌晨三点,那种奇怪的吞咽声又响起来了。
就在隔壁主卧。
我忍着恐惧,轻手轻脚地爬到墙根,透过板壁上的裂缝往那边看。
屋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。
爹坐在床边,脸色惨白得吓人,比那个死人还要白。
他解开了手腕上的纱布。
那只手腕上,密密麻麻全是刀口,有的结了痂,有的还在往外渗血,像一条条红色的蜈蚣。
爹面无表情地拿起刀,在旧伤口上狠狠一划。
鲜红的血瞬间涌了出来,滴进下面的碗里。
碗里早就放好了黑色的药粉,血液滴进去,瞬间沸腾起来,冒出诡异的白烟。
那个哑巴就直挺挺地坐在床上,贪婪地盯着那碗血。
爹接了满满一碗,脸色灰败得像个死人,颤巍巍地把碗递过去。
“喝吧……喝了就能留下来……”
哑巴捧起碗,大口大口地吞咽。
随着血液下肚,她原本僵硬如木头的身体,竟然慢慢软化了下来。
她伸出舌头,舔掉嘴角的血渍,那动作灵活得像条蛇。
突然!
她猛地转过头,死死盯着我偷窥的那条缝隙。
这次她没笑。
她张开嘴,露出被血染红的牙齿,喉咙里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。
“啊!”
我吓得尖叫一声,跌坐在地。
紧接着,主卧的门被猛地撞开。
爹冲了进来,手里还提着那把带血的刀,眼神凶狠得像恶鬼。
“谁让你看的!找死吗!”
他一把揪住我的头发,把我往墙上撞。
“我不是让你老实待着吗!你想害死全家是不是!”
我拼命挣扎,哭喊着:“爹!那是妖怪!她在喝你的血啊!你会死的!”
“闭嘴!闭嘴!”
爹根本听不进我的话,把我狠狠摔在地上,转身锁死了柴房的门。
那一夜,我抱着弟弟瑟瑟发抖。
我认定爹是被妖孽迷了心窍,或者这根本就是他在练什么邪术续命。
第二天一早,我从门缝里看到,家里养了十年的老黄狗死了。
就死在院子当央。
全身干瘪,像被什么东西吸干了血液。
而那个哑巴,正蹲在死狗旁边,用袖子擦着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