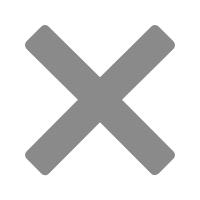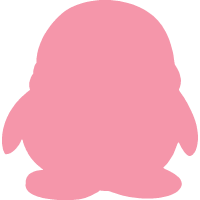3
我必须逃。
再不逃,我和弟弟都会变成那条老黄狗。
爹背着背篓去了后山,说是去采药,其实我知道,他是去给那个妖孽找“补品”。
那个哑巴坐在堂屋门口晒太阳,一动不动。
这是唯一的机会。
我把弟弟绑在背上,用剪刀一点点撬开了柴房那扇腐朽的窗户。
翻出窗户的那一刻,我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。
我猫着腰,贴着墙根往院墙边溜。
只要翻过这道墙,我就能跑到二叔家。
二叔是杀猪匠,身上煞气重,一定能镇住这个妖孽。
近了,更近了。
就在我的手刚刚摸到院墙的时候,一只冰冷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脚踝。
那只手冷得像冰块,力气却大得惊人。
我回头一看,魂都吓飞了。
那个哑巴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,正阴森森地盯着我。
“放开我!你这个怪物!”
我疯狂地蹬腿,可那只手像铁钳一样纹丝不动。
她单手就把我拎了起来,像拎一只小鸡仔。
背上的弟弟被勒醒了,哇哇大哭。
哑巴听到哭声,眼神突然变了。
她伸出另一只手,直直地抓向弟弟的脖子!
她要吃弟弟!
这个念头让我的血瞬间冲上了头顶。
“别碰我弟弟!”
我不知哪来的力气,掏出怀里的剪刀,狠狠扎向她的肩膀。
“噗嗤”一声。
剪刀扎进肉里,没有鲜血喷出来。
伤口里流出的,竟然是黑色的、像墨汁一样的水!
哑巴痛得松了手,发出一声怪叫。
我抱着弟弟摔在地上,爬起来就要跑。
“砰!”
院门被踹开了。
爹回来了。
他一眼看见受伤流着黑水的哑巴,整个人瞬间崩溃了。
“你干了什么!”
爹扔下背篓,几步冲过来,一脚踹在我心窝上。
我被踹得滚出去好几圈,吐出一口酸水。
“你敢伤她!你知不知道她多贵重!你知不知道老子费了多大劲才保住她!”
爹像疯了一样,根本不管我的死活,小心翼翼地扶起那个哑巴,看着她流黑水的伤口,心疼得直掉眼泪。
“作孽啊……作孽啊……”
爹转过身,从杂物房拖出一条拴牛的粗铁链。
“既然你不听话,那就别怪爹狠心。”
他把铁链的一头锁在地窖口的石磨上,另一头锁在了我的脚脖子上。
“爹!我是你亲闺女啊!她是妖怪!她流的不是血,是黑水啊!”
我绝望地哭喊,嗓子都哑了。
爹充耳不闻,抱着哑巴进了屋,给她上药包扎。
隔壁二叔听到动静,扒着墙头往里看。
“老陈,你这是干啥?咋把招娣锁起来了?”
爹抬起头,脸上挂着诡异的笑:“没事,孩子不听话,管教管教。我们在过日子呢,好着呢。”
二叔看着爹那副鬼样子,又看了看屋里那个穿着寿衣的身影,吓得缩回了头,骂了句“疯子”,赶紧跑了。
我瘫坐在地窖口,看着渐渐黑下来的天。
绝望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。
娘,你睁开眼看看啊,爹疯了,这个家完了。
深夜,怀里的弟弟突然浑身滚烫,开始剧烈抽搐。
是高烧!
“爹!弟弟病了!快救救弟弟!”我拼命拽着铁链,把脚脖子磨得血肉模糊。
房门开了。
爹走了出来,但他没有带药,也没有带水。
他从我怀里一把抢过弟弟,转身就往屋里走。
“爹!你干什么!你要把弟弟带哪去!”
爹回过头,眼神冷漠得让我心寒。
“给他治病。”
说完,他把弟弟抱进了那个充满血腥味和尸臭味的房间,抱给了那个喝血的哑巴。